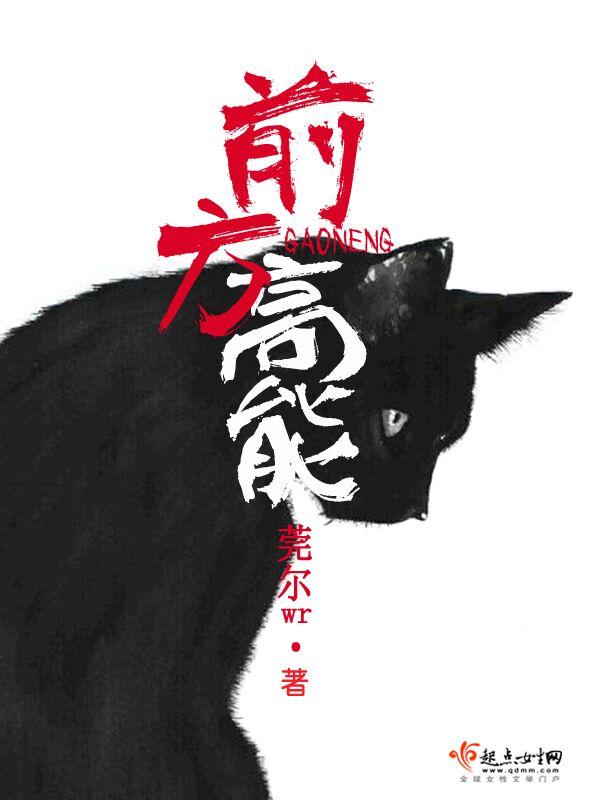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阿姊误我 > 第54章(第3页)
第54章(第3页)
裴厌城又是一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模样,宋舒月找不到人说话,只好掀开帘子去看外面。
大街上人头攒动,无数人想要通过帘子看清马车里的是何人也。
人多,也杂,可宋舒月还是一眼望到了人群中的异类。
蒙面,戴帽,亦步亦趋,看步伐,是个练家子。
宋舒月杀手的敏锐还在,直觉告诉她,不像是冲着钱帛来的。
到了宋府,竟一路无事发生。
宋舒月悬着的心稍微放了放,又自嘲,以前喊打喊杀的日子过惯了,如今有了别的身份,却还是下意识的喊打喊杀。
她真是有病。
合该她杀了一辈子人,最后落不到善终,到底刀尖舔血的人,杀孽太重。
宋府象征性的贴了红喜字,留他们吃了饭,席上宋离月阴阳怪气,说什么无媒无聘,名不正言不顺云云。
裴厌城不说话,句句都受了,最后送了她四个字:“与你何干?”
气的宋离月脸颊红一阵白一阵,又不敢愤然离席,只能生生将尴尬和羞赧忍了下来。
吃罢饭,裴厌城带着宋舒月即告辞。
临走,宋相把宋舒月叫到跟前,捏着她的肩膀道:“皇宫不同寻常人家,你在家如何没有规矩没人敢说什么,到了宫里也该收敛些,不过我儿放心,必能护你周全。”
宋舒月一瞬间有些鼻酸,这些日子以来,她在宫里的日子可谓是尝尽苦楚,整个人就像是个沦陷在深海的孤岛,仿佛怎么走,都是死路一条。
那边马儿嘶鸣,是裴厌城再催促她上路。
于是她阔别家人,出门上了马车。
马车里,裴厌城虽未闭眼,但灰白的瞳仁看起来好像是死鱼眼睛,恐怖又膈应人,她不想直视,索性靠在马车上小憩。
马车悠闲的走在街上,车轮落在青石板上的声音沉闷又频出,她被吵的睡不着,坐起来,支了本游记看。
这时,裴厌城轻声道:“你不问吾为何?”
宋舒月打了个哈欠,随口道:“问什么?”
裴厌城低眉笑道,面上露出一丝玩味的表情:“也不知是你真的如此心宽,还是故意扮做这样。”
宋舒月嗯了一声,抬头朝裴厌城道:“你料定了他们会来?万一不来,岂不是功亏一篑?”
说时迟那时快,一只利箭百步穿杨而来,穿透马车,钉在车后随行守卫的心窝。
裴厌城一点惧色也无,调侃道:“这不就来了?”
只见他随手抄起宋舒月,让她躲在小几的后面,另一只手从车夫手里夺过鞭子,一鞭子下去,马儿吃痛狂奔,那些守卫和杀手的撕打声逐渐消失,尾随而来的,只有五只马的马蹄声。
“五个。”裴厌城耳朵微动,旋即从马车上站了起来,强风吹的他的大氅上下飞舞,他像个游神一般,在街上横冲直撞,从人多的地方,跑到人少的地方。
马车被无方向感的人驾驶,很快没了主意,只好慌不择路,有路就走。
很快他们行驶到一断崖前,身后追兵随即赶到。
五人的脚步声沉稳有力,一看就是高手。
裴厌城从腰间取下剑,但昏暗的光线让他的眼睛更不继事,他只好把剑戳在地上,问了句:“谁派你们来的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