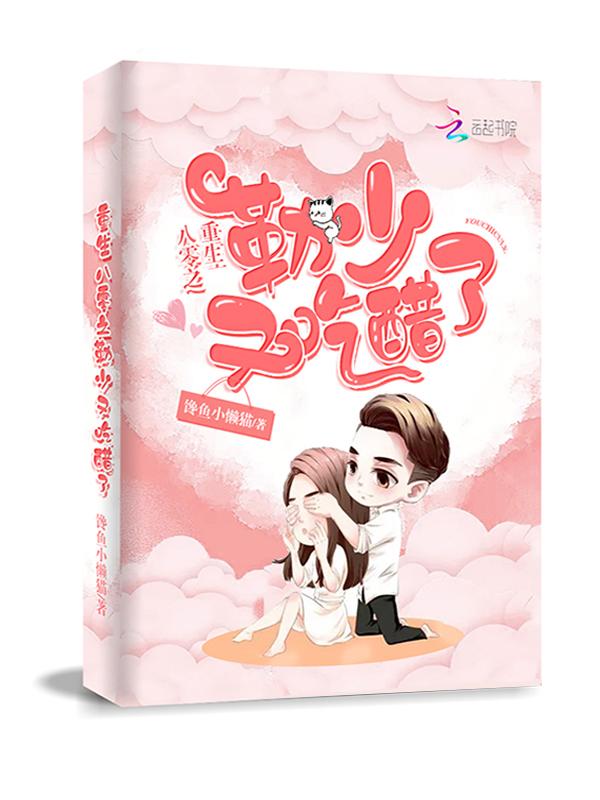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为初恋他爹守寡后 > 弘远(第1页)
弘远(第1页)
话毕,禅院内鸦雀无声,落针可闻。
手下是迅速虬起的肌肉与暴突的青筋,柏姜转头看向褚绍,他面色不变,衣襟底下的皮肤却已经涨得通红,一如他异常暴烈的情绪。
她现下已经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安抚得住褚绍了,心头若有似无萦绕着危险的气息令柏姜的手心微微出了汗。
“含微。”柏姜低声道。
身边没有回应,她偏头看过去,见含微脑门上已经渗出了豆大的汗珠,他不敢出声,无声地比划着:
“药不在我身上,在主子那——”
可是褚绍似乎一点也没有用药的意思。
风雨欲来,空气仿佛凝固,粘稠得令人无法顺畅地呼吸,在手下的胳臂蓄力的一瞬间柏姜终于开口:
“王爷——”
不知哪里刮起一股山魈风,“呜呜”呼号着自山林深处携云带雨而来,“哗”一声将她的兜帽吹下,钗环流苏在回旋的气流中噼啪乱响,一如被惊起的雀鸟。
褚绍动作不停,轻轻挥开了她的手,继而转身捏住她耳边被风吹得猎猎作响的衣料,十分妥帖地替她将兜帽重新戴好,递过来一个“我有分寸”的眼神,柏姜从脸颊边握住他两指,后脑重新被包裹在令人安心的黑暗中。
“大师有什么顾虑,但说无妨。”
那大师没有回答,他合手道了一声“阿弥陀佛”,继而睁开因为苍老而褶皱下垂的双眼,遥遥看了眼天边,又看向柏姜:“贫僧有一些话,须得对这位女施主说。”
柏姜讶异地回看过去,她这一路因为被刻意掩藏的身份,从事藏在人群背后不被人注意,这弘远是什么得道高僧,在这种要命的时候格外提及了她?
那弘远大师眼珠苍老浑浊,平静如海,看不出喜悲嗔怒。
褚绍闻言用力反握住柏姜拉着他的手。
天边一道闷雷劈下来,空气变得越来越黏腻潮湿,要下雨了。
柏姜转头用气音对着褚绍说:“让我去,你看好他们。”
褚绍还是不放手,柏姜来回地抚摸着他拇指上突起的关节:“没堂审没定罪,没到处置他们的时候,你听话。”
箍着的那只手送了些,柏姜趁热打铁,空着的手柔柔地覆上他冰凉坚硬的手背,把自己的右手抽了出来:
“记得用药,回头我要问含微的。”
褚绍不情愿地“嗯”了声,一挥手示意梁毅带人将底下人带去禅房看押起来,含微扶刀小跑着到柏姜与弘远法师交谈的佛堂门外守着。
柏姜进佛堂时空中已经飘起了雨丝,刚又吹了风,刚跪坐在蒲团上就忍不住打了个喷嚏,这要是在小时候可是会被姑母罚抄佛经的,不只是冷得还是吓得,柏姜立刻合手道:
“阿弥陀佛,师傅莫怪,大约是刚受了凉,不是有意冲撞佛祖的。”
她看见对面窗户大开:“早上还只有点云彩,这会儿就刮风打雷的。”
弘远也跟着往窗边看去:“山中气候多变,老衲呆惯了,施主大概一时间适应不来。别看这时候风雨交加,过会儿怕就晴了。”
柏姜点头,没忍住又打了个喷嚏,她无奈地合手道:“……师父,我还是将那窗子合上吧。”
弘远微笑着点头:“无妨,这里穷乡僻壤的,不比皇城规矩森严,施主自便就好。”
柏姜朝门外道:“含微,关窗。”
门外那个顶天高的影子便动起来,把佛堂一圈的窗子关得严严实实,一丝风都吹不进来。
屋里立时暖和多了,柏姜端坐好,理了理衣料间的褶皱,不想对面弘远却扶杖站起来到佛前拈了三炷香递给柏姜,柏姜只得接了,恭恭敬敬在佛前拜了三拜,将燃烧的线香插进香炉里,香气馥郁,仿佛回到了慈安寺的小佛堂。
“大师有什么顾虑,我定会一五一十地转述给摄政王。”
“施主远道而来,不顾舟车劳顿还要来敝寺施粥,可见是个心肠慈软的人。”
“呵呵……”
弘远听她干笑也不说什么,只是娓娓讲道:“施主前几日大概也听身边人提起老衲在外的传言,譬如在雪山下入定七七四十九日、怀中有一颗舍利子之类……都是假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