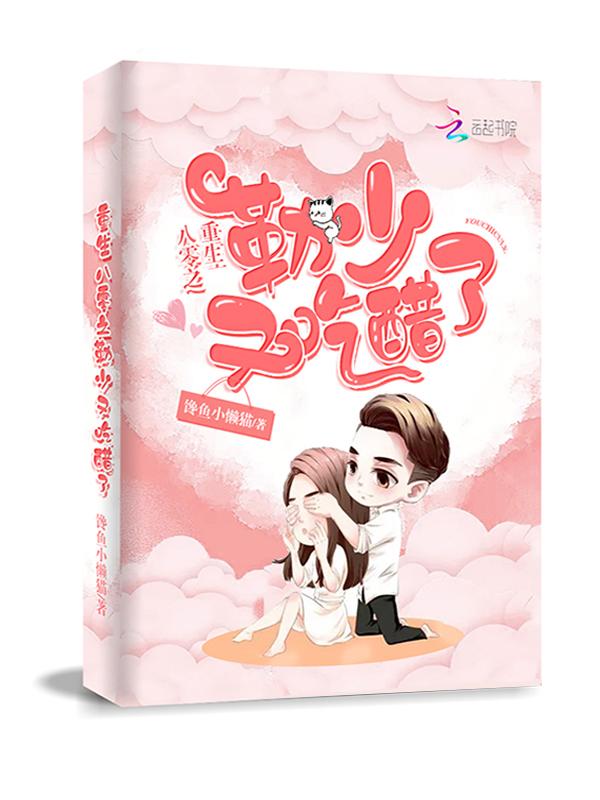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汴京丫鬟被卖后 > 第一百二十六章(第2页)
第一百二十六章(第2页)
“娘!”邵堂喊她,脸上带着笑,一点看不出情绪。
杨桂花远远地哎了一声,脸上的不快一扫而空,欢欢喜喜地将人迎进去。
里正甲正这个时间点也都到齐了,里里外外的人都伸着脖子看这位新出炉的举人相公,心里都对自家村里出了举人而感到与有荣焉。
里正刘伯年过五旬,却看上去精神抖擞,声音洪亮:“邵堂,咱们村里从没出过举人,你是头一个,我们都为你高兴!”
甲正是个四旬方脸的模样,比起刘里正坐地更端正严肃些,却也挂着发自内心的笑脸,与邵堂也是与众人道:“一州七县,一县九乡,乡下头又有十几个村,别说咱们村了,就是整个县,这十几年来的举人都屈指可数,隔壁的吴举人还是早十几年前的事,邵堂,你可真给我们挣脸,咱们绿河村,不,整个河乡,都觉得脸上有光!”
邵堂在邵大伯的引见下,和众人一一见过,并且恭谨请里正甲正、邵大伯等人坐下,说话时并不倨傲,反倒有礼。
这让所有人都用羡慕嫉妒的眼神都看着,心里更是盘算着要不要将自家儿子送去村学读书,将来也好挣个秀才举人,要是能做官吃垧,也就能从此改换门庭,再也不是底层农户了!
……
邵堂在前头待客,朱颜夫妻也没闲着。
邵远抱着灵姐,假意逗孩子,实则望风,见杨桂花也去了灶房紧盯着有无人偷嘴,赶紧示意朱颜从后窗户撬动翻进外头上了锁的主屋去。
没过一会,开了席面,所有人挤挤攘攘地找地方坐下,大多数都是自家带来的桌椅板凳,层次不齐地高矮坐着,可谁也没说什么,毕竟今日邵家大出血,将席面置办地有声有色,除了鸡鸭,还有鱼,以及大猪蹄上剔下来的肘子肉,卤过后散发着香气,勾得人直流口水,哪里还有心思听上头的甲正说废话。
可甲正不结束,谁也不敢头一个举箸挟菜。
过了两盏茶的时候,直到邵堂主动劝酒,这才算终于完事。
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,甲正有事走了,邵近出去送人,乡邻也陆陆续续提着板凳碗筷回去,堂屋里只剩刘里正、邵大伯等还坐着,可不管怎么说话,唯有邵父脸色越来越沉。
只因饭都吃完了,易家的人也没出现,易家的人不来,他想说的话就说不了。
邵堂正好对上亲爹怀疑的目光,却见他似有若无地露出个笑容:“爹?你怎么不高兴?”
所有人都看过来,邵父只能咧开嘴笑,随意找了个借口道:“不是,我是想你上京的路费凑齐没有。”
邵大伯立刻问及。
邵堂道:“多谢大伯父。”说着将二哥一家与他同上京,且尹家做主,二哥帮忙出一些的事说了。
邵大伯顿时尴尬,茶杯往桌上一放:“老二,这是怎么回事?”
是啊,邵堂的路费怎么会由当哥哥的邵远夫妻负责出?邵父邵母是做什么的?难道这几年邵父一分钱没出,皆是邵远两口子供养邵堂读书的?
虽然有些不可能,但邵堂自己都这么说,摆明了要给邵父难堪,谁还敢不信他的?
邵父脸色无以复加的难看,“老三,你胡说八道什么?全家供给你这么久,你就只记得老二的功劳?老二一家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?”
“爹,我只问你一句。”邵堂不跟他啰嗦,直接开门见山,“你是不是给我订了门亲事?”
邵父否认:“什么亲事,你从哪儿听来的?”
邵堂冷笑一声:“你别管我从哪儿听来的,你就说有没有这回事吧!”
朱颜听到吵架声,心道若不是杨桂花去送客还没回,只怕还更有热闹可瞧。
于是让莲花朗哥抱着灵姐出去找小虎玩,拉了邵远两个站在堂屋外头听里头的官司。
原本还乐呵呵的邵大伯和刘里正顿时都愕然。
刘里正不好插嘴,邵大伯主动问:“老二,你真这么干了?”语气里是明显不客气地质问。
邵父心虚地不吭声,心知他脾气的邵大伯察觉不对,问邵堂怎么回事。
邵堂将邵父如何与易家何时定下的婚事,又是打算怎样用这法子拿捏自己,易家又是什么人户一一说了。
邵大伯气得够呛,根本也顾不得有刘里正和晚辈在场了,挥开劝他的邵旺,手指着邵父鼻子骂:“你家里三个儿子,老二踏实能干,老三读书成才,即便老大从前不好,现在也渐渐好了,现下邵堂中了举人,以后扬眉吐气,村里人都只有羡慕你的份,有得是好日子等着你。你瞧瞧你干的什么事?是鬼迷了心窍了还是存心恶心人?你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吗?”
邵父原本只是想拿捏邵堂,谁知变成这样,脸上顿时挂不住,却只哼笑一声,显然恼羞成怒:“我是他老子!我管教他天经地义!你们都帮着他,不就是想沾光?我告诉你们,我养他二十几年要是都吃不到好处,你们更别想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