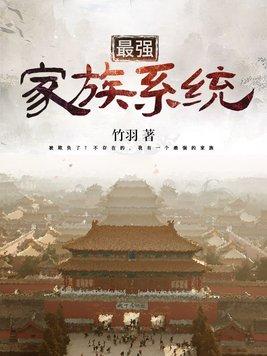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重回和亲祭旗前 > 榻前(第1页)
榻前(第1页)
春光透过窗棂的空隙,洒在了靳淮生的上身。
樊持玉见一屋子人的人都屏息凝神,都以为大夫是要施针。
胡大夫撸起衣袖,摸了摸他那白色的长髯,说了句:“诸位且放心吧,他一会儿就能醒了。”
即便他这么说了,众人也不见得能放下心来。
只见他甩了甩胳膊,似乎是在活动筋骨。
随后两手贴至靳淮生腹部,并没有拿银针。
他的手上有发硬的厚茧,那茧子在靳淮生腹上摩挲,若不是他此刻还在昏睡,定然能感到微微发痒。
那双粗糙的手好像在找什么。樊持玉重新被过身去,不忍再看。
未等众人反应过来,胡大夫便猛地一用力,双手重重地按在了靳淮生上腹。
身边看着的王妈妈见状吓了一跳,呵了一声,赶忙快步上前想要拉开胡大夫。
樊持玉被王妈妈这一呵惊到了,不由得转过身走上前了几步。
未等王妈妈扯到胡大夫的衣袖,樊持玉就见榻上的靳淮生呕出了一口血。
血色是暗沉的,泛着乌光。
樊持玉想起前世末了,她将利刃刺进奚尔训的胸膛和脖颈,那时胸口流出的血也是这般黑中掺杂着暗红,不似脖颈上喷出的鲜血那般艳红。
还未等她细想,她就听见了王妈妈又一声惊呼:“郎主,郎主醒了!”
这一连串的动作太快,从胡大夫猛压靳淮生上腹到靳淮生呕血,再到他睁眼,不过片刻间。
屋内靳府的几人都拥到了榻前。
那位先前去请大夫的小厮是赵管家的义子,向来有眼力见。他察觉到自家主子合上了里衣想坐起来,便连忙伸手去扶。
靳淮生抬手擦了擦嘴角的血,而后又揉了揉额角,掀开褥子,从榻上坐了起来。
他身前立了不少人,其中胡大夫见他已经坐起,便转身去拾掇自己的药箱。
大夫走开后,靳淮生看见了原先被胡大夫宽大衣袍遮住的樊持玉。
见她立在几步之外,神色中的惊心与忧虑一眼就能分辨。
樊持玉和他对上了眼神,她想走近些看看,但又想到此时靳淮生衣衫不整,此时众目睽睽,她贸然靠近,恐怕要遭人闲话。
她没有向前走动,也没有再向榻上看去,只是转身走到桌前坐下,自己拿了桌上倒置的空杯子斟满,而后喝了几口已经凉透的茶。
靳淮生见她没作声响,看着周遭的人脸上神情变得放松,他开口问了句:“现在是几时了?”
床头预备侍候的小厮答了他:“还未到饭点。”
榻上的靳淮生叹了一口气:“都散了吧,午后我还要去郁府议事。”
身边的小厮和妈妈应声退下了,留下樊持玉和靳绮兰坐在桌边,那胡大夫也随着王妈妈和小厮向外头走去了。
樊持玉低头不作言语,靳绮兰仍是满脸忧虑,看了他一眼:“都这样了还不好好歇着,得亏今日母亲没在家,见不着你这死样。”
靳淮生站起来给自己穿衣裳,一边说着:“公事要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