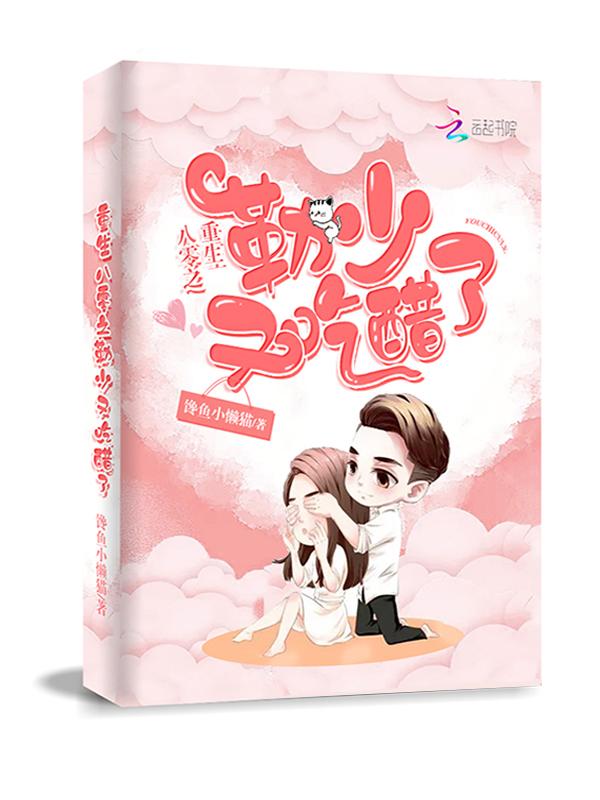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重回和亲祭旗前 > 双星(第1页)
双星(第1页)
樊郅心下惴惴,焦灼不已,唯恐虞安春做些什么断了靳淮生的前途。
他将靳淮生视为重振昌弋侯府的棋子,其心之所向,断不允许这颗棋子在尚未盘活的时刻就被赶出局。
先前管家来传话,是有靳府的小厮前来带话告知。
当李钰恒象征性地询问尚书令虞安春是何意见时,他说:“此议断不可从。”
他有他的立场与考量。
从他尚书令的角度看,此举一是劳民伤财,加重朝廷负担;二是工部户部事务难为,如今夏汛将至,恐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应对;三是此并非急切之事,尚可容后再议。
樊持玉闻此言后蹙眉沉思。
她知道虞安春说的是实话,且前两点理由字字在理。
可惜樊持玉清楚,她与靳淮生都没法向他说明,为什么必须要在今年把这事干成。
八月初安奚就会遣使提起和亲之事,在他们的计谋里,要么和亲拿钱财,要么撕破脸打一仗。
前世半生飘零已经证明了和亲是死局,换不来经年安稳。
而这条计划中的河道,可以在来日的对战中发挥极大的作用,大大增加靖国的胜算。
毕竟如今靳淮生和樊持玉的手还伸不到兵部,顶多旁敲侧击的上言说要练兵尚武,但这样终究不是办法。
她和靳淮生明知来日时局走向,不可能不早做打算,也不可能毫无准备地去赌靖国能否一战功成。
樊持玉轻声喟叹,抬眼见樊郅愁容,心下忽觉惘然,力不能支。
“那您看来,此事还能成吗?”她试探地问了问樊郅。
她如今只是个闺阁娘子,朝堂上的时事,只能从樊郅和靳淮生的言语间窥探了。
“不好说啊。”樊郅摇了摇头,“虞太保此人极为固执,他也算是文官之首,若是他执意如此,那也不好办……”
“更何况如今陛下顾虑的正是他所说的,恐此行劳民伤财。若是如今国库充盈,工部得空,此事还尚有机会。”
樊郅摸了摸下巴,独自言语,自觉如今希望渺茫,不免有些落寞。
总还有办法的。
樊持玉心下暗忖。
此时已是四月初一,前世的涝灾是在夏初时节,约摸是五月份,而关于和亲的圣旨,樊持玉记得很清楚,中黄门临昌弋侯府正是八月十五秋夕日。
也就是说,若是想要这条运河在来日的战事中排上用场,它至少要在中秋前完工。
如今虞安春对此持异议,那么到了来日朝会正式议事,朝中言官多半不会力赞承平帝此议。
只因着虞安春在国子监祭酒的位置上干了数十年,不知当了多少年科举主考。他提拔门生无数,他本人如今也算是朝中的清流之首。
樊持玉在院中独自想着此事难为,忽闻春风,见楝花开了满树,细红如雪。
想到待楝花落尽的时节,永平渠就该涨水了。
又见天边飞鸟过,风振花枝微颤,竟有几簇楝花悄然落下。
那飞鸟在空中盘旋许久。随后又有白鸽振翅前来,俯冲至樊持玉的应然苑。
是靳淮生传信的白鸽。
函胡闻言走来,欲帮樊持玉解下那白鸽的脚环。
樊持玉一时欣然,起身迎了那白鸽,本想自己取信,见函胡前来,便也作罢。
那白鸽脚环内的卷纸小小一簇,函胡小心地将其取出,交给了樊持玉。
她本想帮着樊持玉释鸽于空,谁料那白鸽扑腾了两下,又飞回了樊持玉手边。
无奈,樊持玉只好先放下卷纸,朝着永兴坊的方向,纵鸽向远空。
这回鸽子未作回旋,朝着既定的方向飞去了。
樊持玉拾起卷纸,缓缓展开,见靳淮生亲笔:“吾已有定策,汝切勿忧心,来日再作分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