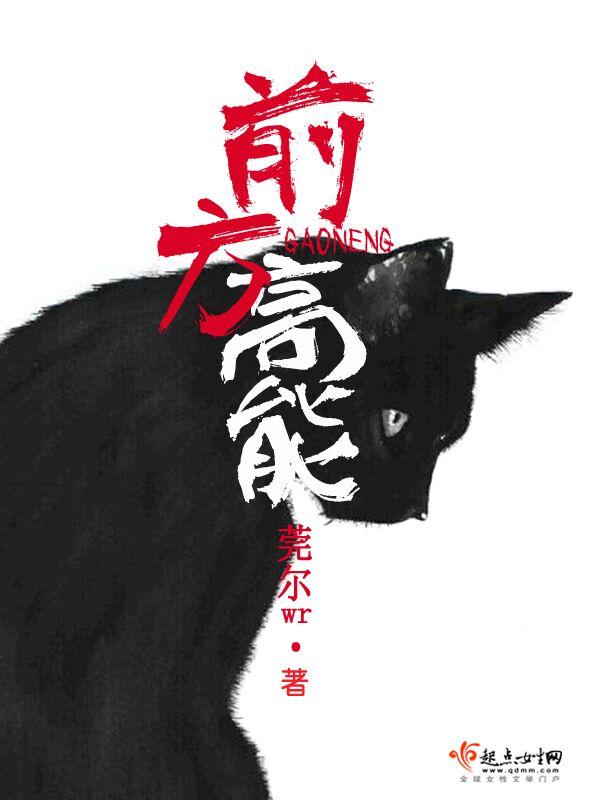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开局一间当铺,它能典当时间! > 第1章 矿工之子苏辰(第1页)
第1章 矿工之子苏辰(第1页)
黑石城的夜从来不是黑的。
那是掺了矿灰的、浑浊的、沉甸甸的灰黑色,像是把天地都塞进了一口熬了百年的药罐子,熬出来的全是呛人的渣子。
黎明前最暗的时刻,苏辰站在自家后院。
说是后院,其实不过三丈见方。地上铺的青石板早被矿尘沁透了,踩上去有种诡异的软绵感。
墙角堆着劈好的柴,码得整整齐齐——这是他十西岁那年父亲定的规矩:练剑可以,但活不能少干。
木剑破空的声音单调而固执。
一下,又一下。
十五岁的少年赤着上身,汗水混着空气中永远飘浮的细灰,在脊背上淌出道道泥泞的沟壑。
他的动作很稳,每一次挥剑的角度都像是用尺子量过,分毫不差。虎口处的茧子厚得发黄,那是五年三千个夜晚磨出来的。
但若仔细看,他右手的食指侧边,却有一小块浅淡的墨迹。
那是白天帮父亲记账时沾上的,洗不彻底。
“第一百三十七。”
苏辰心里默数,木剑斜撩,手腕微转,剑尖在将将要触到晾衣杆的瞬间收回。杆上挂着的粗布衣裳纹丝不动,只震落几粒积尘。
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,嘶哑得像破了的风箱。黑石城醒了——或者说,这座城从来就没真正睡过。
深井里的挖凿声、运矿车的铁轮碾过碎石的摩擦声、守夜人拖着步子走过的咳嗽声,这些声音混在一起,成了黑石城的呼吸。
沉重,疲惫,带着铁锈和血的味道。
苏辰收了剑,用井边破木桶里的水草草擦了身子。水是灰的,映不出人影。他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,推门进了堂屋。
灶台冷着,锅里剩着半碗昨夜的杂粮粥,己经凝成了糊状。
他坐在门槛上等。
天光一丝丝从东边挤出来,却穿不透永远笼罩在黑石城上空的矿尘雾。那些光挣扎着洒下来,成了昏黄的、病恹恹的颜色,照得整座城像个巨大的坟场。
脚步声从巷口传来,很沉,每一步都像要把地踩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