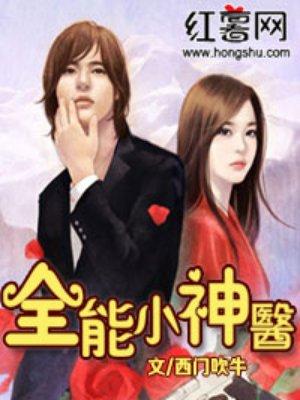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冥府任职录 > 第 58 章(第2页)
第 58 章(第2页)
天宫上下,惟有掌灯宫女和值守侍卫醒着。但与别处不同的是,流华宫和化乐宫双双灯火辉煌,不见人安寝。
蔺沧已焦躁地摇着着扇子在重华殿门口踱步了成百上千个来回,流华宫里上上下下堪用的宫女、侍卫、仙官都被他赶了出去,每隔一会儿便陆续过来回报。如此听了大半夜的消息,却仍不知孟元的踪影。
约莫戌正三刻的时候,化乐宫祁连氏的几个元君派人来问乐缨的去向。彼时蔺沧正闲在重华殿里作画,自他被少泽下了禁令后,他便成日待在流华宫里懒得出去见人,即便是孟元,他这些时日也见得不多,更不必说乐缨。
祁连氏人禀告说因着平日里家教极严,乐缨定会在戌正前回来,不知今日是为何,便来此处寻一寻。她们未得到有用的消息,也便告退了。
那会儿蔺沧没太当回事,毕竟这年纪的孩子贪玩,一会儿忘了时也是有的。直到了亥时,蔺沧身边的掌事仙官管彦急急地上来报,说是孟元此时还未回到流华宫,蔺沧这会儿方才上了心,想是二人玩在一处去了。
他虽知晓这二人的性子,但如此深夜了还玩在一起总归是不好。何况方才祁连氏派人来询问,可见已是找了一些地方。蔺沧忙吩咐人上下找一找,尤其是天冥宫处。想着总归是能找到,便继续回殿中作着画。
不料,管彦禀告说天宫上下各处除了天尊天后宫里,旁的都皆一一问了话,均无乐缨和孟元二人。蔺沧方才停笔蹙眉,觉得此事有些蹊跷。两个对天宫并不熟悉的几万岁年纪的人,怎的能藏得无影无踪,总不能藏到少泽那处。
他只想着是这些宫人办事不力,便亲自出去寻了一寻,上至三十三天、下至七重天,都未见二人踪迹。
他寻得久了,管彦劝他且在重华殿等着消息,若这桩事原是小事,许仅仅是二人吃醉了酒歇在了某处,但若惊动了天宫上下,恐怕天尊那儿要怪下罪来。蔺沧虽不在乎少泽如何做想,但的确不能为着此事让孟元成为众矢之的,便依话在重华殿等着。这一等便等到了后半夜。
今夜不知为何夜色犹凉、风露极重,饶是蔺沧都加了一件外袍在身上。即便如此,他还是在殿内坐不住,只在殿外如此等着,以便第一时便能得知二人的消息。
他正蹙着眉听完宫女的回话,一个面生的小仙官却不经通报急急忙忙地闪躲开守宫门的天将,疾跑到蔺沧身前时一个滑跪跪倒叩拜,未等蔺沧说话,他焦急道:“还请殿下快去化乐宫!我家仙君撑着一口气有话对您说!”
蔺沧一愣,霎时间闪身到了化乐宫。
还未等他入殿,便嗅到空中有一丝血腥之气,他心头一紧,急急忙忙地踩云步直入殿内。殿中烛火极盛,一层又一层的人围在一榻边,多是女子,各个满眼堕泪、妆容尽失。这一群人见了蔺沧赶来,忙急急地让出一条道来。
蔺沧快步走入,见那榻上直直地躺着乐缨,面色苍白污脏、发丝凌乱,华服上下尽染尘土与血迹,斑斑血迹或黑或红,多是已干涸了几个时辰的陈血,新鲜的仍不断地涌出来,连那榻上都染得血红,触目惊心。
如雷击一般地,蔺沧的脑海蓦然空了一瞬。
他只扫这伤势一眼,大约能知晓是何处之人所为。
榻边的圆凳上坐着一衣衫精致的中年女子,原是乐缨的姑姑,是当日孟元在七重天上看到的坐在马车中的贵妇人。她早已是泪如雨落,哭得一双眼睛犹如两个核桃般的红肿。
她见了蔺沧,忙起身带着哭腔道:“方才南天门天将来禀告,乐缨不知被何人扔在了地上,如今正追查着。这孩子浑身是伤,这是造了什么孽!还请殿下快些听听他要说什么,他撑着一口气不肯我们动他,说是只等殿下来了才肯安心。”
蔺沧径直到了乐缨的榻前,尽力平定下自己的情绪,沉稳道:“有我在,你且慢慢说。”乐缨已是血色尽失,呼吸时断时续,见着蔺沧到来,他方才努力睁开眼睛,呼吸霎时间急促起来,下一刻便止不住地咳起了血。
乐缨嘶哑道:“出去。。。。。。出去。。。。。。” 他说话时激动不已,新一轮的痛楚又如潮水般袭来。这句话用了他此时全部的气力,即便如此,乐缨仍挣扎着睁大了眼,急急地等着蔺沧开口。
乐缨姑姑焦急地看着蔺沧,手中细腻光滑的帕子已被不停地揉捏攥紧。蔺沧眉头紧锁,只道:“你们且都先下去,传药师殿的人在殿外候着。”一声令下,这一众女子虽仍是噙泪不舍离去,但见蔺沧如此,还是鱼贯出了门去。姑姑泪眼婆娑地看了乐缨好几眼,方才在侍女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。
一时间殿内除了乐缨、蔺沧二人外,再无他人。
乐缨胸膛剧烈地起伏着,面色比先前又苍白了三分,额上已密密地沁了豆大的汗珠,他咬紧牙关,忍着身上一阵阵袭来的剧痛。蔺沧急忙坐至榻边,迅速地拿起乐缨的手腕把了脉,眉蹙得越来越深。
片刻后,他将双指从乐缨时而微弱时而急促的脉上移开,捻诀在几个穴上一阵连点。蔺沧努力克制住自己心中的慌乱,沉着声问乐缨道:“孟元呢?”乐缨的经脉平稳有力起来,身上的痛楚亦是消减了大半。
但听到“孟元”二字时,他浑身的气血再次上涌,霎时间吐出一大口血来。蔺沧心跳瞬间一滞,脑中一声嗡鸣。他方才已经暂时定住了乐缨的经脉,半个时辰内不会有皮肉之痛。即便如此,乐缨眼下的反应竟如此之大,难不成孟元。。。。。。。
蔺沧的双手渐渐握紧,指尖因用力而发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