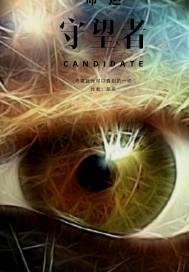第七小说>小花成熟时 > 3040(第34页)
3040(第34页)
—
温杭挂完电话,身体支撑不住,倒下去睡着了。
迷迷糊糊睡了会,有一瞬间,她头发变短,身体缩小,脸蛋发起稚气的婴儿肥,仿佛回到多年前的午后。
上着课发烧了,闻初晴扶着她去校医室打点滴。
温杭躺在病床上,夏日浓长,半阖着眼,能看见的窗外香樟树荫,外面校医和闻初晴在交谈。
校医:“通知家属了吗?”
闻初晴:“她妈妈没空,我就是家属。”
校医笑了下:“你算个什么家属。”
闻初晴:“我算她姐姐。”
温杭半醒着,听见对话,悄悄抬袖口擦眼睛。
闻初晴端着杯水过来,看见温杭掉眼泪,她脸上着急:“怎么哭啦,身体不舒服?”
温杭睁开眼,阳光斜淌进房间内,在她脸上镀层暖色,心情由阴转晴,温杭摇头笑了笑,又忽而哽住声。
“你真好,像天使。”
麻醉效力过了,额头上撕裂的痛感卷土重来,她眼睁开半扇,目光没有焦点。
许多细枝末节在梦里无法呈现,但她听见闻初晴脆声回答。
“我好,你也很好。”
“你要相信,是你足够好,才能吸引别人。”
缥缈梦影里,那张灿烂的脸停在眼前,睽违已久,跟铭刻于心的旧时光一同席卷而来,温杭恍然,半撑起身,懵然看着,沉沉呵出一口白雾。
“小初,你来梦里看我了是吗?”
眼泪随着声音从眼角淌落,吧嗒坠落到手背上,她望向门口,感官失真,眼前有散不去的潮湿迷雾,真真假假,被想象击得溃败。
下一刻,许柏安推开门进来,驱散一室雾气。
模糊的视线骤然清晰,温杭惊醒,心头淤青,所有痛感一瞬强烈,瘦削双肩发抖,像枯枝上即将败落的花苞,摇摇欲坠。
许柏安走近,看清她婆娑泪眼,顿了下:“怎么哭成这样?做噩梦了?”
——是美梦才是。
混沌感消弭,她嗓子涩疼,急切摇头,带着压抑的低泣声,真的难过,像高压锅找到唯一的出气口宣泄。
“许柏安,你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,非得这个时候进来。”
洇红眼尾抬起来瞪他,泪朦朦的,含酸涩情绪:“你知不知道我的梦没做完!”
“你脑子摔坏了?”话不好听,但他单手扣住她发顶,动作温柔地把人揽进怀里:“我怎么知道你在做梦,那么不讲理?”
她哽着音腔大口艰难呼吸,许柏安叹了口气:“别哭了。”
他身上有匆忙奔来,风尘仆仆的清冽味,温杭倾身抱住他,泄愤一般把眼泪鼻涕都蹭到他衣服上:“哭怎么了?眼睛是我的,我想哭就哭!”
许柏安替她顺了顺背,试图讲道理:“你没脑子吗?弱者才会掉眼泪,哭难道能解决问题?”
“哭是不能解决问题,那我不哭,我也解决不了啊,我哭一哭怎么了,碍你眼了。”
她咬紧下唇,委屈又骄横:“你道歉。”
她牙齿咬唇咬得用力,就快出血,许柏安她捏住下巴,指腹去摩挲唇瓣:“松口。”
温杭慢慢松开,水汽潮湿的眼跟他对视,许柏安有那么几秒心疼,用指腹揩走她眼角的泪,第一次有失原则认下错。
“行,是我不好。”
温杭不喜欢哭,但人总有情绪崩盘的时候,根本控制不住。
等她情绪平复,许柏安第一件事就是要她手机。
温杭解了锁屏,茫然递过去:“你要干嘛?”
他淡淡:“设个紧急联络人。”